主 管:上海市司法局
主 辦:上海市律師協會
編 輯:《上海律師》編輯部
編輯委員會主任:邵萬權
副 主 任: 朱林海 張鵬峰
廖明濤 黃寧寧
陸 胤 韓 璐
金冰一 聶衛東
徐宗新 曹志龍
屠 磊 唐 潔
潘 瑜
編 委 會:李華平 胡 婧
張逸瑞 趙亮波
王夏青 趙 秦
祝筱青 儲小青
方正宇 王凌俊
閆 艷 應朝陽
陳志華 周 憶
徐巧月 翁冠星
黃培明 李維世
吳月琴 黃 東
曾 濤
主 編: 韓 璐
副 主 編:譚 芳 曹 頻
責任編輯:王鳳梅
攝影記者:曹申星
美術編輯:高春光
編 務:許 倩
編輯部地址:
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 號均瑤國際廣場 33 樓
電 話:021-64030000
傳 真:021-64185837
投稿郵箱:
E-mail:tougao@lawyers.org.cn
網上投稿系統:
http://m.bjxh8388.com/wangzhantougao
上海市律師協會網址(東方律師網)
m.bjxh8388.com
上海市連續性內部資料準印證(K 第 272 號)
本刊所用圖片如未署名的,請作者與本刊編輯部聯系
從知青到律師:時代洪流中的法治堅守
宋小紅律師訪談摘要
2025年第05期 閱讀 18 次
采訪時間: 2018年7月23日
受訪人:宋小紅
采訪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我們和宋小紅是多年的老朋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熟悉了,她所在的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與我們市律師協會曾同在中山南二路03招待所里辦公。當時,本市一張市級大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共和國的同齡人》的文章,專門介紹了幾位上海律師事業恢復重建階段最早的優秀實習律師,宋小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我們很高興將她請來,聽聽她的經歷和當年的創業故事。
宋小紅:我是1968屆的初中生,進中學不到一年,“文革”就開始了。1969年1月,我跟著1966屆、1967屆的學生一起上山下鄉,去安徽插隊落戶,被分到淮北最貧窮的靈璧縣。務農1年9個月后,我被推薦到靈璧縣的服裝廠。在那工作4年后,恰逢黑龍江省軍區到安徽征女兵,很多農村干部的女兒都想當兵,而當時我因父母還沒有平反,入伍的希望很小。巧的是,之前在當地水庫游泳時,我奮不顧身地救了一個接近水閘、險些被水流吸附吞沒的小孩。武裝部政委見我水性這么好,就邀請我去教士兵們游泳,所以在征兵時極力推薦了我。于是,沖破層層阻力后,部隊終于把我帶走了。
到了部隊,我被分在黑龍江省軍區哈爾濱211醫院,新兵訓練了一個月后被分到警衛班。我們三個女兵(其中兩個上海兵)工作特別認真,不到探視時間不允許任何外人去病房探視,曾將政委、司令員都攔在外面。一年后,我受到了軍區的嘉獎,之后被調到院務處當文書,負責寫材料。我是1973年的90個新兵里第一個入黨的,之前還有個插曲:我因不愿按照有關領導的要求作出立即與父母劃清界限的書面承諾,被調到211醫院炊事班去鍛煉,負責300多個病人的伙食。本應有15個人的編制,僅給我安排了6個人,明擺著是整我。但我起早摸黑,切菜做飯,硬是完成了任務。后來又把我調到干部病房,由于長時間清晨4點起床,加上腳上穿的大套鞋經常因泡在水里全部濕光,沒過多久,我就病倒了。經初步診斷,我患了免疫系統的一種綜合癥,據傳屬不治之癥,部隊很緊張,同意我回上海治療。在部隊整整6年后,我病退回到上海,后該病漸漸痊愈。
上海市的安置辦將我安排在上海城建學院(后來并入同濟大學)實驗室工作。一段時間后,得知市律師協會/市第一法律顧問處正在籌辦,我前往報名,寫了一篇為何想當律師的申請材料,被正式錄取,于1981年1月前往報到。當初有人質疑我:“你的毛病這么多,能勝任工作嗎?”結果沒有想到,我做律師后沒有請過一天假,從早做到晚,忙著看材料、出庭。1983年“嚴打”時,我經常忙到晚上10點多。可能是運氣好,我的病之后再沒有復發。經查資料,得了這個綜合癥的1萬人里面可能有1人不治自愈。
我剛到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后稱市第一律師事務所)時,在辦案組跟著倪彬彬、陸靜安等老師學辦案。那時還沒有分民事、刑事,開始時民事案件比較多,如離婚、繼承等。后來一處搬到03招待所辦公,民、刑案件分開,民事組由趙珪老師負責,刑事組由倪彬彬老師負責。刑事組人數相對較少,組內有王珉、吳善興、蔣光學、謝圣本、張渝生、王一鳴、汪波等律師和我。很可惜,王珉老師55歲時因病去世,發病時正在法院開庭。開始有法律顧問業務后,一所又成立了經濟組。一所后來還在襄陽路、延安飯店、襄陽北路、巨鹿路、衡山路等地臨時租房辦公,最后搬到淮海中路,才算是時間最長、最穩定的時期。
一所的起步階段非常艱苦,只有三張寫字臺,沒有其他財產。最初,我們的辦案提成比別的事務所少很多,且分配也不合理——刑事案子只能提30%,一般是30元;指定的案件則更少,僅15元;而經濟案子可以提35%~50%。事務所的業務辦理分工很清楚,辦案組負責辦理刑民事案子,法律顧問業務則由經濟組去辦。如果我們接到法律顧問業務,也要交給經濟組,但倪老師和我都從不計較,沒有發生過矛盾。后來律師事務所改制時,有的領導說我們之前錢拿足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脫離實際的。截至改制時,我們積累的幾百萬元資金大部分是靠辦理民、刑案件的30元或15元提成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而我們的工資最高為60元/月,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
我剛到律師事務所時不太愛說話,覺得自己的強項還是寫寫東西。而要當好律師,一定要開口。平時所里開會,倪老師總是鼓勵我,逼我多發言。開始跟著倪老師辦案子時,我總是坐在旁邊聽,當她的助手。我第一次獨立辦案是在徐匯法院,辦理的是流氓集團案,一共10個被告人,印象中我辯護的是第一被告人,倪老師辯護另一名被告人。我開始讀辯護詞時緊張得要命,像被告人一樣,渾身發抖。倪老師她們一再叫我“鎮靜、鎮靜”,但我還是沒有平復下來,講得一塌糊涂。后來經過多次鍛煉,我的膽量越來越大。不限于法庭,我到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時也不再害怕。會見死刑犯時,他們最多只有腳鐐扣著,我也是直接面對面和他們講話,他們大多對我很信任,有些沒跟檢察官交代過的情況都會跟我講。
我們辦理每個案件都要事先做好各種準備工作:摘錄卷宗材料,寫好辯護詞。閱卷摘抄材料時,因為沒有復印機,我們都是手工摘抄的,所以格外仔細、非常認真,每一本卷都摘抄得很厚。有時疊放在地上的卷宗,包括摘抄的材料,都疊到桌子一般高。哪個證據在哪一本卷的第幾頁,我們心里都非常清楚,開庭時在法庭上就可以快速地引用,準確找出被告人與其他被告人、公訴人與被告人、被告人本人前后供述之間的矛盾,有利于案件的正確裁判。
“嚴打”時期,案子集中,閱卷被安排到法官的辦公室里進行。沒有空位時,我們就將一疊疊案卷材料搬到大廳的乒乓球臺上繼續工作,直到摘錄完成、把材料還給法官。我們還將新發現的案件有關情況通報給法官,以期引起重視,從未“開后門”或者搞歪門邪道,那時的人都很單純。我們經常摘抄到晚上11點多才結束,法官們也很盡職盡責,不少當時陪著我們閱卷到很晚的法官后來都當上了基層法院的院長。那時律師與法官的關系很正常,法官對我很客氣,他們確實尊重律師,能夠仔細傾聽律師的意見。我從來沒有給法官送過禮,反而有時閱卷、開庭趕不上吃飯,還是法官去食堂打飯給我吃,而上了法庭后我還是照樣辯護。記得中院有一個案子,幾個律師與法官都是很熟的朋友,我們在庭上辯得面紅耳赤,誰也不讓誰,其他法庭的法官聞聲而來,還以為我們在吵架呢。還有一個案子,對方公訴人后來擔任了某區的檢察長,當時我們辯論的火藥味很足,他氣得拍桌子,大聲說:“宋小紅,我怕你啊?”庭后他還多次到政法委告我。但是一段時間后,我聽說他在檢察院內表示“請律師還是要請宋小紅,辯得真好”。因為他們覺得我沒有私心,就是為了讓法律得到正確實施,大家庭上是對手,庭下是朋友。所以我辦案時,如果覺得有些案子的問題很大,我就直接找庭長談,從來不會去送禮之類的,我覺得這樣做是降低我的人格。
那時候,我覺得辦刑事案子很單純,就是按照《律師法》對律師的要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為了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該怎么辯就怎么辯。我辦案時膽子大、放得開,法官也比較純潔。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市律師協會和法院、檢察院每年都開會交換意見,互相將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來,有關單位很重視,會回去檢查、糾正。不像現在的有些法官對律師制度不理解、對律師有成見,認為我們收當事人的錢,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所以在辦案時,特別是遇到上訴案子,只要有與一審判決書不同的內容,往往就會馬上反駁,不聽律師的意見。
從1983年“嚴打”開始,我辦理了刑案上千件,其中好幾件無罪辯護、十多個無罪釋放,原定判死刑而辯護后改判的有近十人,影響較大,因此在看守所的嫌疑人之間傳開了。有法官告訴我,他去看守所提審時,看到監房內的墻上刻著“宋小紅萬歲”,嫌疑人都說“請律師就請宋小紅”。經不認識的人口口相傳后,我的性別、年齡信息都走了樣,居然有人稱我為“宋老”!有次還引發了一個誤解:我們組內一位律師的案子辦到一半,被告人說“我要換宋小紅辦”,害得那位律師以為我搶了他的業務。刑事案子的一審、二審我都辦,有的二審不開庭,我就遞交認真準備的書面上訴辯護詞。
朱洪超、鮑培倫等第一批法科大學生有很多都在我們一所實習過,都很優秀。作為師姐,我非常支持朱洪超到聯合律師事務所當副主任,讓青年律師參與事務所的管理,這在當年是一大進步。
我辦理過不少影響較大的案子,如某宣傳部原部長潘某反革命宣傳案、楊某反革命宣傳案(與李國機老師合辦)等。在辦理楊某(外籍)案時,王會長、何會長及有關領導明確指示,這個案子以后是要拿到中國駐美國領事館給大學生看的,因為是第一次展示中國律師的形象,要真的辯,不走形式,還要求不作無罪辯護。我把卷宗摘錄后,寫辯護詞時覺得該案不像反革命宣傳罪。于是,我沒有寫“無罪”兩個字,而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辯護,辯護詞送審后通過了。開庭時,對方兩位公訴人中有一位是檢察長,辯論很激烈,還有領導在下面旁聽。事后,法院里有人告訴我,當時一聽我的辯護詞就覺得是無罪辯護。后來楊某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沒多久就被遣送回國,他很感激我們律師。
靜安法院有個起訴投機倒把的案件找到我作無罪辯護,一審判決有期徒刑兩年,被告人上訴到中級法院,被宣判無罪并當場釋放,影響很大。《國家賠償法》出臺以后,被判無罪就很難了,于是有人選擇取保候審,一年以后就自動解脫,不再追究。
還有一件案子,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女兒被原戀愛對象殺害了,市律師協會推薦了一所的趙律師作為被害人的代理人。我們的當事人姓陳,與被害人、殺人犯都很熟,關于其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各方持不同意見:公安認為是殺人共犯,檢察院認為是流氓罪。我反復閱卷后,認為當事人是無罪的,其與殺人犯沒有一點共同故意,也沒有共同行為。我在有政法委領導參與的案件討論會上發言提出,我只針對案件、針對事實,不考慮上下級關系,同時以事實和法律為標準,觀點明確,認為殺人共犯不能成立。因各方對此案的分歧較大,法院決定暫不開庭,先請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終結果不了了之,當事人被無罪釋放。事后,有關領導對此高度評價,認為幸虧充分聽取了律師的意見,沒有判當事人有罪。我很高興,這說明我們國家的法治越來越健全了,應該多一點聽得進不同意見的領導干部,能夠盡量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我的辦案量很大,但從來沒有違紀、缺席,也從未遲到過,我將日程安排都記在了腦子里。
某玻璃廠的陳某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玩忽職守罪,我與張中律師接受事務所的指派,為其作無罪辯護。后來最高人民法院把玩忽職守罪去掉了,而被告人引用公開刊物上的資料卻因有關領導有過批示,原判予以維持,其仍被認定為泄露國家機密罪。所以,有時候,律師也會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遺憾。
我除了辦刑事案子,也辦理一些經濟案件,如代理原告安徽蕪湖長江大橋有限公司訴省電信局的經濟案子。該案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當事人見識了我為此案花的工夫,因此對上海律師非常感激。
據1993年市司法局律管處的統計,我的辦案數量在整個上海律師中名列前茅。然而第二年的4月,我的兒子就闖禍受了重傷。當時我正在法律顧問單位,我幫他們寫了三份訴狀準備起訴,正忙著打印、蓋章,沒有接到電話,耽誤了急救的有效時間,使兒子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感謝事務所在搶救期間幫我支付了部分醫藥費。
2000年,律師事務所進行國辦所脫鉤改制,律師們對于是整所改制還是分所改制的分歧較大。我的觀點是分所改制,且不想陷于矛盾之中,于是帶領我的幾個學生、同事,以及一所開創時期的全部老律師離開了一所,設立了新的律師事務所。
采訪人:從學生到農民、工廠工人,再到應征入伍,轉業后學法律、做律師,宋小紅律師的經歷豐富而坎坷。她于1981年進入本市最早設立的第一法律顧問處,1982年生完小孩沒多久就參加了華東政法大學的自學考試,邊工作邊學習,四年間通過了全部考試。作為當時最年輕的女律師,她師從第一代著名女律師倪彬彬,與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很有名的李國機大律師同臺辯護過,真是難得。在刑事辯護方面,她的名氣非常響。學習時,她刻苦努力,取得成功;工作時,她嫉惡如仇、不講情面、以理服人,贏得尊重。
自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宋小紅律師經歷了律師從無到有、法治從弱到強、重視律師與不尊重律師的現象交替出現的不同年代。從她的回憶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青年律師艱苦的成長之路,以及幾十年來法治環境的局限與不斷進步。她羨慕現在的大學生很早就有了實習、實戰的機會,寄語青年律師要不忘初心,發揚老一代律師為法治獻身的精神風貌;青年律師則可以從她的經歷中學到前輩們一絲不茍、吃苦認真的勁頭。
今天,我們聽了宋小紅律師的人生故事以及她辦理過的難忘案件,非常精彩,意猶未盡。非常感謝宋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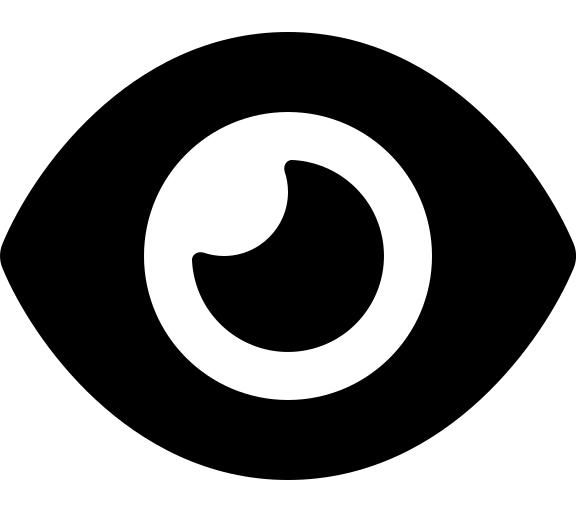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