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不正當競爭糾紛中,被告首先會以雙方有無“競爭關系”否定原告的訴訟資格,法院在判定是否侵權分析中,也常常將雙方是否具有“競爭關系”作為論述的理由,本文分析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關“競爭關系”的立法過程,以及司法實踐中對各種“競爭關系”的判定方法和規則。
關鍵詞:網絡 不正當競爭 競爭關系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與競爭關系
《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其適用上的變幻莫測而著稱,其中競爭關系就成為既復雜又充滿爭議的基礎性問題,始終伴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歷程。“競爭”和“不正當競爭”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是“定海神針”,其界定直接決定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和適用范圍,也決定著法律的具體適用方式。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將競爭關系的有無作為判斷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前置要件。
《反不正當競爭法》(2017年修訂)是對1993年施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首次大修,2019年修正時僅針對商業秘密條款,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自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2025年修訂已呈現淡化“競爭關系”趨勢,如《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7條“關鍵詞隱性使用”、第13條“濫用平臺規則禁止條款”、第15條“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禁止條款”、第14條“平臺壓迫低價禁止條款”。鄭友德教授指出:“反不正當競爭法是行為規制法,不是權利保護法。現代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個重要走向就是突破對競爭關系的制約,既保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又保護沒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可以統稱為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既包括橫向保護經營者或同業經營者之間的競爭利益,又縱向保護上下游經營者之間的利益,還保護其他相關的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為了更好地理解“競爭關系”,2022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2〕9號)(簡稱《反法新司法解釋》)第2條對此進行了明確。根據該條規定,法院可以認定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存在可能的爭奪交易機會、損害競爭優勢等關系的市場主體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規定的“其他經營者”。將“競爭關系”定義為廣義競爭關系,即“存在可能的爭奪交易機會、損害競爭優勢等關系”,對“競爭關系”作出從寬解釋,體現了對實踐共識的遵循,也延續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相關司法政策文件和案例中表明的立場。《反法新司法解釋》的思路與當前法院的審理思路一致,或者說是把司法實踐經驗轉換為司法解釋指引。如大眾點評訴百度地圖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對于競爭關系的判定,不應局限于相同行業、相同領域或相同業態模式等固化的要素范圍,而應從經營主體具體實施的經營行為出發加以考量,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調整的競爭關系不限于同業者之間的競爭關系,還包括爭取交易機會或破壞他人競爭優勢所產生的競爭關系,競爭的本質是對客戶即交易對象的爭奪。因此,在互聯網領域,不論是否是同行業經營者,只要是對交易對象的爭奪可以認定存在競爭關系。
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雖然沒有直接就“競爭關系”的界定進行規定,但已有條款的內容已經體現了對于“競爭關系”的廣義解讀。根據《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第二章“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同行業的直接競爭對手、不同行業但互相爭奪“網絡注意力”或者存在互相損害競爭優勢可能的間接競爭對手、上下游企業、互聯網平臺和平臺經營者之間的競爭行為都可能受《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中相關條款的規制。
《反不正當競爭法》(2017年修訂)關注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屬性和不正當性,是否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和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而不再糾結于競爭關系等的界定,不再將其作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和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前提要件。或者說分為兩個步驟,即競爭行為的定性不需要考慮當事人之間是否具有競爭關系,只需要考慮是否為市場競爭行為,然后根據諸如第二條第一、二款之列的要件認定其是否正當。但是,在不正當競爭民事訴訟中,原告必須證明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是否存在同業競爭關系可以作為認定是否可能造成損害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此基礎上確定原被告之間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即原告資格的適格性。事實上大多數不正當競爭確實發生于同業競爭者之間。即便如此,競爭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確定是否具有損害并不一定是限于同業競爭。行政執法只考慮是否構成競爭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更無需特別界定競爭關系了。
即使《反法新司法解釋》實施以后,會讓司法審判實務對競爭關系的認定爭議縮小,但因網絡競爭案件的復雜性,仍然會存在一定爭議。在現代《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視域下,盡管競爭關系在判定不正當競爭行為中的功能被削弱,但在司法實踐中,競爭關系仍被視為審理不正當競爭案件的邏輯起點,在不正當競爭案件中仍有確定原告資格的特殊意義。
二、直接和間接競爭關系的判定
(一)直接競爭關系
法院對“競爭關系”的判定大體上作兩種分類,一是直接競爭關系,二是間接競爭關系。所謂競爭關系,指市場主體之間在競爭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直接競爭關系通常是指市場經營者從事相同或類似的經營業務,直接競爭關系對應的市場主體就只是同一行業的經營者。在瀏覽器轉碼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原告和被告均屬于從事互聯網閱讀服務的經營者,在互聯網文學市場上存在直接競爭關系;在搜狗輸入法搜索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原、被告之間具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競爭關系,理由是原、被告均經營搜索引擎業務,在服務內容、用戶群體、盈利模式等方面有所重合。上述案件在認定直接競爭關系時,法院將關注點置于原、被告屬于相同行業或者具有相同的經營范圍,并以經營者之間提供同質性或替代性商品、服務作為認定標準。
有研究者對2000年至2020年法院審結的122件互聯網新型不正當競爭案進行統計和梳理發現,122件案件中被法院認定為直接競爭關系的案件就有84件。由此可見,在互聯網新型不正當競爭案件中,認定直接競爭關系的案件仍占大多數。另有研究者對2000年至2018年京、滬、粵三地法院審理的176件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案件進行梳理,僅有26件案件裁判未明確論述訴爭雙方之間是否存在市場競爭關系。認定為直接競爭關系的案件有80件,認定構成間接競爭關系的案件有31件,未明確說明訴爭雙方存在競爭關系的有11件。從數量上考察,被法院認定為具有直接競爭關系的案件依舊占大多數,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訴爭雙方僅通過直接競爭關系的認定就可以解決訴爭焦點;二是在實踐中直接競爭關系的范圍超出了學界所定義的范圍。
(二)間接競爭關系
對于間接競爭關系的界定,我國司法實踐進行了一定的探索,概括起來可以分為經營行為標準、競爭利益標準和用戶群標準。經營行為標準如大眾點評訴百度地圖案、競爭利益標準如“極輕模式”深度鏈接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用戶群標準如“暴風影音”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如果僅以直接競爭關系作為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前提,可能導致其他市場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因不正當競爭行為受損卻無法受到保護,無法實現《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宗旨。因此司法實踐中對競爭關系的界定也相對寬泛。“小拇指”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并未限制經營者之間必須具有直接的競爭關系,也沒有要求其從事相同行業。經營者之間具有間接競爭關系,行為人違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的,也應當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再如“幫5淘”購物插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指出:“在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市場主體從事多領域業務的情況實屬常見。對于競爭關系的判定,不應局限于相同行業、相同領域或相同業態模式等固化的要素范圍”。在“世界之窗瀏覽器”屏蔽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原、被告的經營范圍雖不同,但兩者均通過網絡實現其經營目的,享有共同的網絡用戶,存在利益交叉,因此應界定為具有競爭關系。百度與青島奧商搜索不正當競爭案中,就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競爭關系的問題,法院認為雖原、被告的服務類別不完全相同,但原告實施的在百度搜索結果出現之前彈出廣告的商業行為與被告的付費搜索模式存在競爭關系。該案例明確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競爭關系”不再局限于同業經營者之間,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與此同時,該案例也暗含競爭關系是認定不正當競爭的前提這一規則。
值得關注的是,從整體趨勢上觀察,法院對間接競爭關系的認定和運用正漸成一種趨態,比如,在“千尋影視”屏蔽廣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就認為,互聯網行業的出現及蓬勃發展催生了諸多新的經營方式,若僅將競爭關系的范圍囿于直接競爭關系,恐難實現《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故此,在互聯網新型經濟業態下只要雙方在最終利益上存在競爭關系,便可認定他們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此一推論無疑擴大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范圍。
間接競爭關系也成為認定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基礎。然而間接競爭關系缺乏準確的法律定義,在具體適用中幾乎完全依靠法官的論述說理。這樣導致的結果之一是,經營者的不正當行為如果損害到其他經營者正當經營活動,即使不屬于同一行業或服務類別,都會認定二者存在間接競爭關系。這就意味著“間接競爭關系”的外延會因自由裁量而無限擴大。從宏觀層面看,互聯網環境下每個市場參與者之間都可能存在競爭關系。
搜狗“搜索候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在互聯網環境下,網絡經營模式的多樣性發展以及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交織,使得市場界限日趨模糊,業務領域存在交叉或關聯的企業之間均有可能產生市場競爭。
三、廣義和狹義競爭關系的判定
(一)廣義競爭關系
由于網絡環境下經營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已經從傳統狹義的同業競爭關系,擴大到經營主體之間在市場競爭中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關聯關系,甚至經營主體存在利用或爭奪他人在市場中形成的競爭優勢的行為,都將被認定為經營者之間存在競爭關系,即廣義的競爭關系。司法實踐以各種理由和說法擴張競爭關系的解釋,實質上已使競爭關系成為虛置,且擴張的理由越來越牽強,其實際目的無非是為了擺脫競爭關系在認定不正當競爭中的傳統束縛,也說明競爭關系確已成為不必要的束縛和障礙,實現競爭關系的突破勢所必然。通過此種方式放寬競爭關系的界定,雖然可以階段性地及時應對法律調整的復雜局面,看似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仍然掣肘于是否可以滿足競爭關系要件的矛盾中。
《反不正當競爭法》(2017修訂)第2條將“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這一要件改為“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放寬了原法中對損害法益的限制。因此,有學者認為,損害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和無競爭關系的消費者都在被禁止之列,不再受“是否具有競爭關系”這一要件的制約。《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2條增加了“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但包含的含義與未修訂前無實質性變化。
(二)狹義競爭關系
在互聯網環境下,競爭雙方的差異越來越明顯,它們在經營體量和規模上相距甚遠,甚至連主營業務也不盡相同。當前諸多互聯網競爭行為中,參與競爭的市場主體已從一種直面彼此、直接競爭的關系逐漸演變為依附、寄生的關系。如陸金所金融服務平臺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為例,該案中兩原告系國內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頭部企業,其經營的陸金所金融平臺擁有龐大的投資者群體和較高的知名度。而被告則是一家提供計算機技術服務的小微企業,與兩原告之間并無業務交集,在經營規模上亦不足以相抗衡。由此可見,無論市場主體在行業內處于何種量級,其在互聯網環境下都可能成為特定細分領域的競爭者,這在傳統的不正當競爭糾紛中并非常態。
在載和“幫5淘”購物插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對競爭關系的本質進行了論述:競爭關系包括狹義的競爭關系和廣義的競爭關系。前者是指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具有同質性及相互替代性的經營者之間的同業競爭關系,后者是指非同業經營者的經營行為之間損害與被損害的關系。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市場主體從事跨行業經營的情況實屬常見,互聯網環境下的行業邊界更是漸趨模糊,故不應將競爭關系局限于同業競爭者之間的狹義競爭,而應從經營者具體實施的經營行為出發加以考量。競爭的本質是對客戶即交易對象的爭奪。在互聯網行業,將網絡用戶吸引到自己的網站是經營者開展經營活動的基礎,培養用戶黏性是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因此,即使雙方的經營模式存在不同,只要具有相同的用戶群體,在經營中爭奪與相同用戶的交易機會,亦應認定存在競爭關系。
王先林教授指出:“事實上,《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也沒有明確地限定競爭關系。現在的法院案例包括最高院的指導性案例,都不再強調經營者間一定具有競爭關系,也不一定得屬于同一行業。”
【注釋】:
1、上海律協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專業委員會主任、廣東華商(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2、王艷芳:《<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競爭關系的解構與重塑》,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2期。
3、戴龍、郝俊淇、譚冰玉:《〈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重大問題學術研討會綜述》,載《競爭政策研究》2017年第4期。
4、參見一審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8號民事判決書。
5、孔祥俊:《論新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時代精神》,載《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
6、參見孔祥俊:《<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原理(原論)》,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 119 頁。
7、種明釗:《競爭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8、一審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442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9)京73民終2040號民事判決書。
9、一審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4135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終字第2200號民事判決書。
10、盧純昕、徐馳:《互聯網不正當競爭認定中競爭關系地位的實證研究》,載《法治論壇》第62輯。
11、參見陳兵:《互聯網經濟下重讀“競爭關系”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意義——以京、滬、粵法院2000~2018年的相關案件為引證》,載《法學》2019年第7期。
12、參見吳太軒:《互聯網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法律規制的實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頁。
13、一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8號民事判決書、二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滬73民終242號民事判決書。
14、一審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5)石民(知)初字第3572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終字第02210號民事判決書。
15、一審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2)石民初字第2951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終字第5729號民事判決書。一審認定侵權,二審改判不侵權。
16、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終字第0046號民事判決書。
17、一審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63號民事判決書、二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7)滬73民終198號民事判決書。
18、一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7)京0105民初70786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8)京73民終558號民事判決書。該案一審判決不侵權,二審改判侵權。
19、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魯民三終字第5-2號民事判決書。
20、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滬73民終54號民事判決書。
21、參見一審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2017)滬0110民初12555號民事判決書、二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8)滬73 民終420號民事判決書。該案件為2019年上海法院百例精品案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參考性案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不正當競爭典型案例(2015-2020)之五、2018年“中國十大最具研究價值知識產權裁判案例”。
22、祝建軍:《網絡不正當競爭侵權成立的考量因素》,載《人民司法》2019年第10期。
23、王艷芳:《<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競爭關系的解構與重塑》,載《政法論壇》2021年第2期。
24、寧立志:《〈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得與失》,載《法商研究》2018第4期。
25、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9)滬0115民初11133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佳案例(2020)之一。
26、一審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962號民事判決書、二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7)滬73民終197號民事判決書。該案件為上海法院2015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之案例三。
27、戴龍、郝俊淇、譚冰玉:《〈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的重大問題學術研討會綜述》,載《競爭政策研究》201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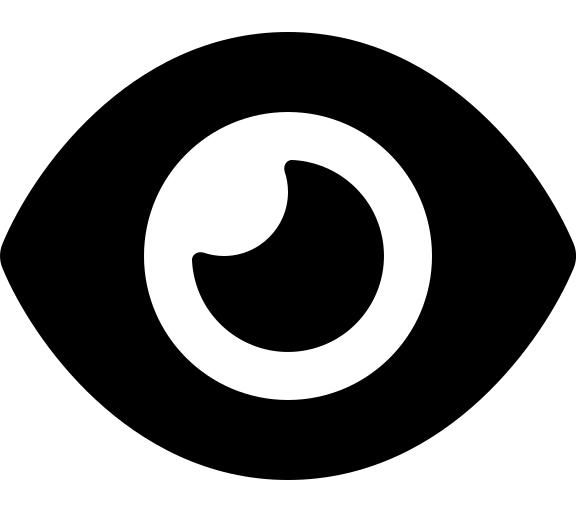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中國律師身份核驗登錄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